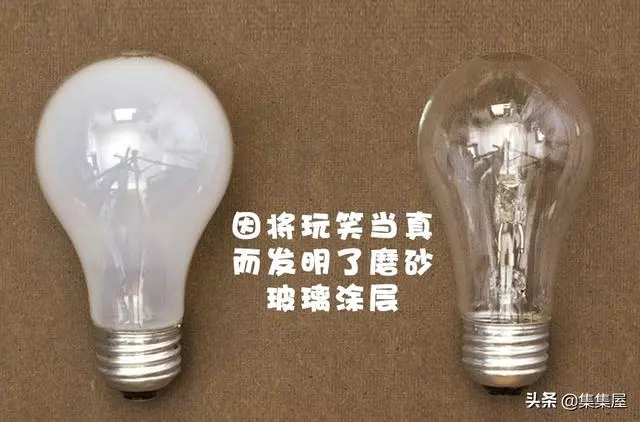中美食品和葯概念差與譯差
 經常見到:某某中藥被美國FDA批准上市,對這句話中國人與美國人的理解不相同。此“葯”非彼葯。中國人認為,這就表明這個中藥被美國官方認可是“藥物”,其地位等同於青黴素,絡活喜等處方西藥,可以“治病”。美國官方理解,這個產品被認可是一個可以上市的食品(或者營養品補充劑),其地位等同於食品,維生素,不可以“治病”。某位中醫生將被FDA抽查,朋友們提醒他,查的時候一定要說,這些都是營養品,食品補充劑,不是藥物,不能治病。也就是說在美國4萬名左右的中醫生們開的中藥,官方,或者說法定認可的,它們只能是不能治病的營養補充劑。所以,在美國,“中藥”不是“葯”。(1)“吃”的東西在美國只有兩個分類,食物和藥物。FDA(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是食品(Food)與藥品(Drug)管理局。是管理食品和藥品的官方機構。吃的東西在他們那裡,只有兩類:食物,藥物。藥物的功能是治病,全是化學品,基本沒有自然產物,只有醫生可以開給病人,叫做處方,只有藥店可以買到。也就是說他們認為,只有人工合成的化學品,才能治療疾病。他們在治療疾病的問題上是把人完全當作化學的,物理的人來對待的。只有化學藥物(把人當作化學的人)和手術刀(把人當作物理的人)能夠解決他們認為的人的“疾病”。食物的功能是療飢,是自然產品,基本沒有化學合成的,擺在食品店裡,大家隨便買,有錢就行,不需要任何條件。這類食物不能有“藥物”作用,有藥物作用那叫有“毒”。我們講的中藥,基本上是自然的產物,目前為止,無法用他們的方法在西醫實驗室里以化學方式證明其能“治病”,只能歸到食品這個類別里。所以在他們的官方概念里中藥和食物是一樣的,它不能“治病”,被統稱為食品補充劑(supplements).藥品有“毒”,那是天經地義的,是治療疾病當中的副作用,由醫生控制,他們可以大大方方的寫在藥物的說明裡,傷肝,傷腎,脫髮,食欲不振,劇烈咳嗽……仔細看一看那些藥物說明書,哪個化學藥物是沒有“毒”的?可是人們還不是照樣吃?因為它能“治病”,即使它們在治病的同時也傷人,致病。病人有知情權與選擇權,即:必須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讓病人知道,這個葯“有毒”(被柔和的稱為副作用),這叫知情權;吃不吃是病人的選擇,沒中毒,是你運氣好,中毒了,別怪沒告訴你,這叫選擇權。還有一層意思,如果你怕副作用而選擇不吃這個葯,那麼你的病情加重,甚至死亡與醫生無關。法律玩兒到這個水平,這是我從當時法律還是低水平的國家來到這裡以後很多年才悟出來的道理。因此病人面對的是“無奈的選擇”,在疾病的風險與藥物的風險之間作出決定。食物不能有任何毒副作用,因為它們放在商店裡什麼人都能隨便買到,不需要任何處方,所以不能有劇烈的副作用。當然這也要有基本的生活常識,一頓吃一斤鹽那行嗎,“鹽吃多了還能齁死人哪”。(2)“吃”的東西在東方人的觀念中分為三類,食物,自然藥物和化學藥物自古以來東方人概念中吃的東西兩大類是食物與藥物,那時候的藥物僅僅是未經化學提成的自然藥物,大部分是植物葯,也有少部分動物葯與自然礦石等,簡稱為中藥。那時候的中藥--自然藥物,絕對是治病的,中國人憑著應用自然藥品治病繁衍了巨大的東方民族。自從3百多年以來,西方化學藥物闖進中國,我們東方人在觀念上,把吃的東西分為三大類:1,食物;2,中藥(幾千年應用的自然藥物),;3,西藥。也就是說藥物有兩大類:中藥(自然藥物或有機藥物)和西藥(按照西方藥理分類化學提取過的化學藥物)。這裡的草藥,東方人的概念中其實是medicine,而不是supplement,強調它們是以治病為目的的。幾百年前中國人來到美國,希望沿用自己習慣的中藥,即可以自用也可治人。可是中國人概念中的草藥在美國沒有這個分類,把中藥作為美國人概念中的藥物進口是根本不可能的。中醫先驅們為了讓中藥能夠進入美國市場,就把中藥稱作食物Food或者食品添加劑Supplement,也對呀,大棗,枸杞,桂圓……皆是葯食通用,這才打開了美國的中藥市場,至今仍然沿用這個管理規定。概念上比較一下:東方——食物(食物)藥物(中藥,西醫化學葯)西方——食物(食物,中藥)藥物(西醫化學葯)(3)中藥概念差帶來的理解混亂形成了中藥濫用與禁用的尷尬局面中藥,對於美國來說,它是食品添加劑Supplements,它受食物法規管理,不能“有毒”,不能有治病的作用,有治病的作用就成了“毒品”。在美國的進口海岸,發現中藥“有毒”的時候,我們的中藥被他們象鴉片一樣焚毀,見本人譯文“麻黃禁令的影響有多大”。根據食物法規,目前按食品或健康營養品市售的中藥,不能在標籤中稱為“藥物”,並且不準註明或暗示可以治療或預防某種疾病。中藥,對於中國來說,“有毒”,那是天經地義的,所謂“是葯三分毒”,因為中國人2-5千多年來是使用中藥治病的,在中國人的概念里,中藥等同於西藥,它是“藥物”,不是食物。所以《內經·五常政大論篇第七十》有言:“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我們承認治病的中藥是有副作用的,所以中國人的生活常識是:“沒病不亂吃藥”。很少有不懂中藥的中國人到藥店自己買葯吃,都是醫生開出方子,到藥店“抓藥”。不象美國人認為的那樣,中藥(Supplements)不需要醫生處方,擺在食品柜上,任何人都可以隨便買,隨便吃。中國人絕對不會把麻黃放進點心裡,當作減肥的食品,而美國人這樣做了。中國人不會拿起半夏珠,當花生豆一樣吃,我親眼所見,美國人這樣做了。中藥是否可申請FDA批准變成他們概念中的“葯”呢?可以,只要您按照藥物(drug)的申請程序,完成生化,藥理,動物實驗,臨床實驗等等,中藥就可以變成藥物。但是這個藥物已經“變味兒”了。不僅僅是從自然草藥變成了化學品,最主要的,第一,他們並不按照中醫理念辨證論治應用,而是按照止痛,降壓,降糖,消炎,利尿等西醫藥理分類開給病人;第二,因為它們是治病的,所以只能由有處方權的西醫用這些葯,懂得這些藥物應用的中醫醫生無權用這些葯;第三,這些葯不能在食品店出售了,只能在藥店里拿西醫醫生處方買。也就是說,中藥變成了西醫化學藥物。如果所有中藥都走這條路子,中藥就真的只是新西藥的“草稿紙”了。例如,早年咱們的紅曲米膠囊被放在貨架上當作食品添加劑出售,因為有降膽固醇的效果,曾經被熱賣。後來其化學提取物洛伐他汀(lovastatin),1987年作為降脂新葯由FDA批准上市,成為西藥他汀類降膽固醇西藥。於是在美國的“紅曲米製品”就被要求拿掉這個成分,否則不能出售。這是美國FDA的警告:“FDA指出,由於三種紅曲米產品含有未經批准的藥物成分,因此相關公司必須停止銷售,否則將採取強制措施。消費者如出現相關不良反應,應求助於醫生。”看,紅曲米從自然發酵食物變成化學提取物以後,美國人概念從食物變成了藥物,管理法規就變了;中國人似乎沒什麼感覺,因為在中國人概念里紅曲米本來就是葯。FDA禁用中藥的名單年年都在增加,日本的一個中藥廠商說,“也許有一天我們會回到只能用針灸,不能用中藥,或者說‘無葯可用’的局面。”再例如青蒿素衍生物變成抗瘧葯。屠呦呦等科研人員研製青蒿素衍生物獲得了諾獎。這種獲諾獎的是什麼葯呢?按照西醫藥物分類應用,它是抗瘧葯,也就是說它已經變成了西方語境中的“Drug”,而不是按照中醫“清熱解暑,除蒸,截瘧”來應用的中藥。中國人看不出什麼區別,因為在中國,中醫西醫都可以開處方葯。在美國區別可大了,老百姓買不到了,他被放在藥房里,中醫醫生不可以用,必須有西醫醫生的處方才能買到。《科學網》聶廣博客,轉載了訪談美國FDA植物葯藥理生藥專家審評員竇金輝博士的文章“中藥‘赴美’作Ⅲ期臨床,離新植物葯上市還有多遠。”這裡的“赴美‘作Ⅲ期臨床”的“中藥”,是中國意義上的中藥,在中醫理論指導下應用的中藥,使用者是中醫生。但是經過I期,II期,III期臨床試驗等過程以後再上市的“葯”,已經不是中國概念的“中藥”了,它變成了西醫處方葯,也就是說,赴美作Ⅲ期臨床而最後上市的並非“中文語境中的中藥”,而是“西文語境中的藥物”。中藥在這裡僅僅是新西醫處方葯的原始材料。這應該是喜,還是憂呢?文章引用竇金輝所說,“青蒿素類葯成為首選抗瘧葯,拯救了百萬兒童的生命。它的起跑線是從中醫藥開始的,青蒿素衍生物已經不再是中藥,但是屠呦呦教授從中醫藥的歷史用藥受到啟發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摘自《中藥“赴美”做Ⅲ期臨床,離新植物葯上市還有多遠》|遇見竇金輝2015-11-02零捌叄期)從我自己的診所來看,20年前主動尋求Herbs者大概占門診的70%,包括湯藥和丸藥,現在主動尋求湯藥的已經基本上沒有了,丸藥應用量也大大減少。我主動開給他們,也要費一番口舌:“我只從美國大的合法的食品公司買這些食品補充劑,從來不會從中國直接買,如果有毒,在美國進口海岸會被檢查出來,根本進不來,我也買不到。”即使這樣說,有不少時候還是會被拒絕,或者委婉的拒吃。有的病人,給他一瓶中藥,應該吃8天,但是過3個月他還會說,“謝謝你,你給我的Supplement我還有,還在吃,”那我就明白了,這是委婉的拒絕,不會強迫他們吃。20多年來,經過“麻黃有毒”,“中藥有腎毒性”,“中藥可能導致癌症”等一波波宣傳,人們的概念已經從20多年前“自然產品,沒有毒,比西藥安全”,改為現在“這些自然的東西,成份不明,可能有毒,不能吃”。他們能夠接受寫在藥物說明裡面的正大光明的“毒”,有幾個美國人不吃任何西藥的?看看哪些藥品說明,哪個沒“毒”?不能接受中藥這種“不明不白的毒”。很不願意看到的事情正在中國發生,似乎中國也要學習美國這樣,把中藥當作食品添加劑來管理。問題的核心是:“人類能不能用自然產物作為藥物來治療疾病”?把人體完全按照物理與化學結構來研究的西方思維,找不出一條“途徑”,一種方法(tool),來實現這個想法。吃的東西“,按照美國這樣分為二類更”科學“,還是按照中國概念分成三類更”科學“?冷靜的從人類健康這個大前提出發,起碼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總體來說,中藥的副作用比化學藥物的副作用要緩和得多,”精通“中西藥的”明白人“自己生病會先試中藥,不效再用西藥;醫學模式從局部向整體的轉化,單純的生物醫學模式正在慢慢轉化到社會心理生物醫學模式,那種把人當作化學與物理結構來治療的思路早晚會變。所以”吃的東西“分三類,或者藥物分成兩類,化學藥物,自然草藥,這是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目前的問題就是兩個:一是整個世界分類概念的改變,在食物與藥物之間加出一個”自然藥物“的類別,承認某些自然產品是可以治病的,必須由懂得它們的人處方管理。二是其研究方法不能循西醫研究方法的老路,完全化學分析,雙盲實驗,也不能完全是中醫的經驗醫學和哲學推理;要找到一種讓西醫和中醫都能接受的”雙贏“方法,即讓西醫”服氣“,不得不”承認“,又能讓中藥堂而皇之的治病,而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似乎有點兒”偷偷摸摸“的造福人類。一個是分類的概念,一個是研究的方法。這是目前雞同鴨講中藥所處尷尬局面—問題的關鍵。(4)中美中藥譯差自從西醫”闖入“中國,譯差就開始了,而且從來沒有徹底”明白“過。據毛嘉陵《第三隻眼看中醫·百年”洋相“》中,”’西化‘的12個是是非非“,其中第一個是非就是”’禍‘起西醫術語的’中譯名‘“page83。他講到了中醫心肺等臟腑概念與西醫不同。我就想到當年中醫基礎課上,王宏圖老師講”脾為後天之本“,有學生問:”你講脾為後天之本,為什麼有人因病切除了脾臟,仍然可以生活得很好?“王老師的回答至今印象深刻:”我們中醫的脾就不在那兒長著。“人們中經常流傳著許多模糊說法,例如有位78歲的老年人慢性腎衰竭,每天吃黑芝麻,自稱黑芝麻”補腎“。其實,衰竭的腎是西醫的腎,黑芝麻補的腎是中醫的腎。且不說慢性腎衰竭該不該吃黑芝麻,就這個問題的提出,已經有概念混淆。西醫理論腎衰竭該不該吃黑芝麻,講的是蛋白質攝入多少不增加腎的負擔,從黑芝麻的蛋白質含量分析;中醫是從黑入腎的中醫理論角度來說黑芝麻補腎。人類學的看法,”人類學前輩,吳文藻先生曾說,用中國話談論西學,必然已經對學科實行了’中國化’“,引自王銘銘所著《人類學是什麼》Pag5。反過來說,用英文談論中國文化,必然也已經對中國文化實行了西化。這個觀點用來理解目前”中醫中藥“在中美雙方醫學與文化中的尷尬局面再合適不過了。也就是說,一種學科被從它誕生的語言環境,翻譯到非其母語文化環境的時候,就已經深深地打上了新語言文化環境的烙印。”葯“,這個詞,在中文語境中,我們已經用了幾千年,它的概念已經打上了中國文化的烙印,如上一節所述,它是東方概念的”葯“。西方Medicine,Medication,Drug,這些詞也已經用了幾百年,它也打上了西方文化,西醫學的烙印。”直譯“所帶來的概念差,把現在的”藥物“概念弄得十分混亂。這屬於中西方文化習俗不同,醫學體系不同,法律準則不同,國家管理條例不同,翻譯不能完全精準造成的。我把它稱作”譯差“,源自於”概念差“。即翻譯和概念不同造成的理解差異。中藥湯劑被翻譯成”茶“(Herbal Tea),我給某個20歲男孩開的”茶“,被他的媽媽喝了,她說:”太難喝了,他不喜歡,我就替他喝了,免得浪費。“我解釋,那是葯不是茶。她說:我知道,No pain,no gain,只要對健康有好處,我不在乎苦一點兒。再解釋,這種”茶“,每個人是不一樣的。她盯著我看了一會兒,說:”下次去商店看看哪種茶適合我。“哎,那個思維,它就走不到一起,光是碰出火花。英文中的:”Drug,,Medication,Medicine,Prescribed medicine,Herbs,Herbal Medicine,Over counter Medicine,Supplement“在翻譯的時候全可能被翻譯成”藥物“。可在英文語境中的概念,千差萬別。Medicine泛指醫或葯,用得比較廣泛。Medication泛指藥物,藥劑,用得也比較廣泛,大部分人的基本概念中仍然是化學藥物。因為美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各個不同民族根據自己的文化背景,對它的理解有區別。Drug是治病的,一般指化學藥物,作用強烈,必須有醫生處方。Suppliment是食品補充劑,它不能治病,不能有強烈的副作用,維生素屬於這類,全世界各個不同民族的草藥如果被批准上市,都在這個類別。Over counter Medicine是非處方葯,擺在藥房里,大家可以隨便買,其作用比處方葯要輕得多,類似中國人概念中的維生素,一般的止痛片,退燒藥等等。Herbs是草,沒有葯的概念;Herbal supplement草做的食品補充劑,也不被用來治病;Herbal Medicine這是一個非官方用語,為了把東方概念中”葯“的含義放進去,也想說它們不是”食“。這個詞沒有官方解讀意義,很多中醫師對病人這樣說,大家都這樣用。美國人也懂,但是與他們的”drug“概念還是有區別,頂多他們會理解為維生素之類的”Over Counter Medicine“;Herbal Medicine再翻回中文”草藥“,又變成中文語境的”葯“了,中國人會理解為”葯“,即西方的Drug,其實那不是同一個概念。諾將頒獎給屠呦呦老師時,您注意那個英文稿,他們可以用”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因為”Medicine“的概念比較廣泛,但是講到青蒿素的時候,就是”anti-malariadrug artemisinin“,抗瘧化學葯青蒿素。他們特別希望外國藥廠多多研究中國的草藥,目的是什麼呢?”approval ofnew drugs“,是發現和批准新的西醫化學葯。一般來講,在法律與官方管理概念上,中藥與治病的西藥絕對不是一回事,準確地說,現階段,中藥只能被翻譯成:Herbs,herbal supplements。維生素在中文裡面,你也可以叫做”葯“吧,也輔助某些疾病的治療吧,但是與洋地黃,青黴素,氯沙坦等處方葯不一樣。在美國銷售的中藥都不是FDA(美國食品和藥品管理局)批准的”藥物“,它根本就不是”葯“,一般是以食品補充劑名義進口。因此,開中藥方,不需專業執照認可,誰都可以開中藥方。中藥在美國作為食品和膳食補充劑上市出售有法律明文規定,不可提及其醫療功能。FDA出台《天然植物藥品研究指南》(草案),對中藥的開發也提出了一種不同常規藥品的管理方式:”(a)允許中藥在保證質量控制的前提下,可以以多種成分混合製劑形式進入臨床開發。(b)在美國已按飲食補充劑形式上市,或已有他國臨床資料,FDA將放寬對該葯臨床前研究的要求。通過臨床申請認可後,可直接進入臨床開發。(c)如果通過對照性臨床試驗,證實其安全、有效,便可被FDA批准為新葯。“請注意這最後的兩個字,”新葯“,它已經變成了Drug。也就是說,說來說去,就是Food變Drug。沒有我們東方人分類中的草藥這個概念。(5)”譯差“造就的一個新興的行業。我曾經應朋友之託,幫她了解在中國熱賣的xxxx中藥,被稱為美國FDA批准上市的中藥,在美國的銷售情況。我去了兩個最大的藥店:Walgreen和CVS,店員根本沒有聽說過,也沒有賣過。又去了本地的中藥店,也沒有見到。問過我自己有相同疾病的病人,他們也沒有聽說過。回來用英文上網查,沒有見到。用中文一查,真是熱鬧,確實如朋友所說正在熱賣。仔細研究一下那個”上市“的批准文件,那就是一個允許生產和銷售食品的”公文“。由此我知道,似乎現在有一種新興的行業,中國人在美國有些營養品生產或者加工廠,主要從中國大陸進口某些中草藥進行加工,成為美國的”營養補充劑“,返銷回中國,就成了這些”中藥已經被FDA批准上市“。這些產品在美國的主流藥店,食品店和英文網站是看不見的。美國的”老百姓“根本不知道,而在中文的網址上鋪天蓋地。或許因為,①國內市場大,有比較大的需求;②國內人現在比較有錢,生意好做,比較好賺錢;③人們在心理上對國內的產品有不信任感,怕假,怕上當,怕有毒;④人們在心理上對美國的產品比較信任,只要說是美國進口的,就比較相信,比較好賣。它的特點是:國內熱,國外冷;中國人熱,美國人冷。他們打了一個”譯差“,”概念差“。無論如何這個”擦邊球“打得好,對中美雙方的GDP發展都有貢獻,給美國創造了可觀的就業機會,為中藥找到了更多市場,而作為醫生我只看效果。中醫藥的概念差與譯差造成了目前中藥一定的濫用與禁用的後果。不過話又說回來,發展靠的是機會,中藥概念差與譯差為中醫中藥按照自己的模式在美國開拓發展帶來了機會。完全按照美國思維及法規那麼中藥是進不來的,完全進入西方思維與法規在美國發展,中醫藥就變味了,權宜之計只能目前這個樣子。2000年6月30日,本地中文報紙,《達拉斯新聞》《達拉斯時報》同時刊登了本人的一篇文章”中草藥急需立法“,從此一直呼籲:把有較強毒副作用的中藥列出清單,作為”特殊管理食品補充劑“,只能由美國執照針灸師應用。這在美國,自從”麻黃有毒”事件以後FDA是有先例的。當時FDA有文件,麻黃可以由針灸師在診所裡面用,因此也是目前可行的一步棋。長遠看,中美中藥概念融合,這似乎也是關鍵舉措。美國是一個法制國家,任何法律,法規的建立或更改靠的是人力,財力。人力靠的是利益與共識,財力目前中醫肯定差得遠。還需要更多同道與民眾清醒認識狀況,理解處境,共同努力。
經常見到:某某中藥被美國FDA批准上市,對這句話中國人與美國人的理解不相同。此“葯”非彼葯。中國人認為,這就表明這個中藥被美國官方認可是“藥物”,其地位等同於青黴素,絡活喜等處方西藥,可以“治病”。美國官方理解,這個產品被認可是一個可以上市的食品(或者營養品補充劑),其地位等同於食品,維生素,不可以“治病”。某位中醫生將被FDA抽查,朋友們提醒他,查的時候一定要說,這些都是營養品,食品補充劑,不是藥物,不能治病。也就是說在美國4萬名左右的中醫生們開的中藥,官方,或者說法定認可的,它們只能是不能治病的營養補充劑。所以,在美國,“中藥”不是“葯”。(1)“吃”的東西在美國只有兩個分類,食物和藥物。FDA(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是食品(Food)與藥品(Drug)管理局。是管理食品和藥品的官方機構。吃的東西在他們那裡,只有兩類:食物,藥物。藥物的功能是治病,全是化學品,基本沒有自然產物,只有醫生可以開給病人,叫做處方,只有藥店可以買到。也就是說他們認為,只有人工合成的化學品,才能治療疾病。他們在治療疾病的問題上是把人完全當作化學的,物理的人來對待的。只有化學藥物(把人當作化學的人)和手術刀(把人當作物理的人)能夠解決他們認為的人的“疾病”。食物的功能是療飢,是自然產品,基本沒有化學合成的,擺在食品店裡,大家隨便買,有錢就行,不需要任何條件。這類食物不能有“藥物”作用,有藥物作用那叫有“毒”。我們講的中藥,基本上是自然的產物,目前為止,無法用他們的方法在西醫實驗室里以化學方式證明其能“治病”,只能歸到食品這個類別里。所以在他們的官方概念里中藥和食物是一樣的,它不能“治病”,被統稱為食品補充劑(supplements).藥品有“毒”,那是天經地義的,是治療疾病當中的副作用,由醫生控制,他們可以大大方方的寫在藥物的說明裡,傷肝,傷腎,脫髮,食欲不振,劇烈咳嗽……仔細看一看那些藥物說明書,哪個化學藥物是沒有“毒”的?可是人們還不是照樣吃?因為它能“治病”,即使它們在治病的同時也傷人,致病。病人有知情權與選擇權,即:必須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讓病人知道,這個葯“有毒”(被柔和的稱為副作用),這叫知情權;吃不吃是病人的選擇,沒中毒,是你運氣好,中毒了,別怪沒告訴你,這叫選擇權。還有一層意思,如果你怕副作用而選擇不吃這個葯,那麼你的病情加重,甚至死亡與醫生無關。法律玩兒到這個水平,這是我從當時法律還是低水平的國家來到這裡以後很多年才悟出來的道理。因此病人面對的是“無奈的選擇”,在疾病的風險與藥物的風險之間作出決定。食物不能有任何毒副作用,因為它們放在商店裡什麼人都能隨便買到,不需要任何處方,所以不能有劇烈的副作用。當然這也要有基本的生活常識,一頓吃一斤鹽那行嗎,“鹽吃多了還能齁死人哪”。(2)“吃”的東西在東方人的觀念中分為三類,食物,自然藥物和化學藥物自古以來東方人概念中吃的東西兩大類是食物與藥物,那時候的藥物僅僅是未經化學提成的自然藥物,大部分是植物葯,也有少部分動物葯與自然礦石等,簡稱為中藥。那時候的中藥--自然藥物,絕對是治病的,中國人憑著應用自然藥品治病繁衍了巨大的東方民族。自從3百多年以來,西方化學藥物闖進中國,我們東方人在觀念上,把吃的東西分為三大類:1,食物;2,中藥(幾千年應用的自然藥物),;3,西藥。也就是說藥物有兩大類:中藥(自然藥物或有機藥物)和西藥(按照西方藥理分類化學提取過的化學藥物)。這裡的草藥,東方人的概念中其實是medicine,而不是supplement,強調它們是以治病為目的的。幾百年前中國人來到美國,希望沿用自己習慣的中藥,即可以自用也可治人。可是中國人概念中的草藥在美國沒有這個分類,把中藥作為美國人概念中的藥物進口是根本不可能的。中醫先驅們為了讓中藥能夠進入美國市場,就把中藥稱作食物Food或者食品添加劑Supplement,也對呀,大棗,枸杞,桂圓……皆是葯食通用,這才打開了美國的中藥市場,至今仍然沿用這個管理規定。概念上比較一下:東方——食物(食物)藥物(中藥,西醫化學葯)西方——食物(食物,中藥)藥物(西醫化學葯)(3)中藥概念差帶來的理解混亂形成了中藥濫用與禁用的尷尬局面中藥,對於美國來說,它是食品添加劑Supplements,它受食物法規管理,不能“有毒”,不能有治病的作用,有治病的作用就成了“毒品”。在美國的進口海岸,發現中藥“有毒”的時候,我們的中藥被他們象鴉片一樣焚毀,見本人譯文“麻黃禁令的影響有多大”。根據食物法規,目前按食品或健康營養品市售的中藥,不能在標籤中稱為“藥物”,並且不準註明或暗示可以治療或預防某種疾病。中藥,對於中國來說,“有毒”,那是天經地義的,所謂“是葯三分毒”,因為中國人2-5千多年來是使用中藥治病的,在中國人的概念里,中藥等同於西藥,它是“藥物”,不是食物。所以《內經·五常政大論篇第七十》有言:“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我們承認治病的中藥是有副作用的,所以中國人的生活常識是:“沒病不亂吃藥”。很少有不懂中藥的中國人到藥店自己買葯吃,都是醫生開出方子,到藥店“抓藥”。不象美國人認為的那樣,中藥(Supplements)不需要醫生處方,擺在食品柜上,任何人都可以隨便買,隨便吃。中國人絕對不會把麻黃放進點心裡,當作減肥的食品,而美國人這樣做了。中國人不會拿起半夏珠,當花生豆一樣吃,我親眼所見,美國人這樣做了。中藥是否可申請FDA批准變成他們概念中的“葯”呢?可以,只要您按照藥物(drug)的申請程序,完成生化,藥理,動物實驗,臨床實驗等等,中藥就可以變成藥物。但是這個藥物已經“變味兒”了。不僅僅是從自然草藥變成了化學品,最主要的,第一,他們並不按照中醫理念辨證論治應用,而是按照止痛,降壓,降糖,消炎,利尿等西醫藥理分類開給病人;第二,因為它們是治病的,所以只能由有處方權的西醫用這些葯,懂得這些藥物應用的中醫醫生無權用這些葯;第三,這些葯不能在食品店出售了,只能在藥店里拿西醫醫生處方買。也就是說,中藥變成了西醫化學藥物。如果所有中藥都走這條路子,中藥就真的只是新西藥的“草稿紙”了。例如,早年咱們的紅曲米膠囊被放在貨架上當作食品添加劑出售,因為有降膽固醇的效果,曾經被熱賣。後來其化學提取物洛伐他汀(lovastatin),1987年作為降脂新葯由FDA批准上市,成為西藥他汀類降膽固醇西藥。於是在美國的“紅曲米製品”就被要求拿掉這個成分,否則不能出售。這是美國FDA的警告:“FDA指出,由於三種紅曲米產品含有未經批准的藥物成分,因此相關公司必須停止銷售,否則將採取強制措施。消費者如出現相關不良反應,應求助於醫生。”看,紅曲米從自然發酵食物變成化學提取物以後,美國人概念從食物變成了藥物,管理法規就變了;中國人似乎沒什麼感覺,因為在中國人概念里紅曲米本來就是葯。FDA禁用中藥的名單年年都在增加,日本的一個中藥廠商說,“也許有一天我們會回到只能用針灸,不能用中藥,或者說‘無葯可用’的局面。”再例如青蒿素衍生物變成抗瘧葯。屠呦呦等科研人員研製青蒿素衍生物獲得了諾獎。這種獲諾獎的是什麼葯呢?按照西醫藥物分類應用,它是抗瘧葯,也就是說它已經變成了西方語境中的“Drug”,而不是按照中醫“清熱解暑,除蒸,截瘧”來應用的中藥。中國人看不出什麼區別,因為在中國,中醫西醫都可以開處方葯。在美國區別可大了,老百姓買不到了,他被放在藥房里,中醫醫生不可以用,必須有西醫醫生的處方才能買到。《科學網》聶廣博客,轉載了訪談美國FDA植物葯藥理生藥專家審評員竇金輝博士的文章“中藥‘赴美’作Ⅲ期臨床,離新植物葯上市還有多遠。”這裡的“赴美‘作Ⅲ期臨床”的“中藥”,是中國意義上的中藥,在中醫理論指導下應用的中藥,使用者是中醫生。但是經過I期,II期,III期臨床試驗等過程以後再上市的“葯”,已經不是中國概念的“中藥”了,它變成了西醫處方葯,也就是說,赴美作Ⅲ期臨床而最後上市的並非“中文語境中的中藥”,而是“西文語境中的藥物”。中藥在這裡僅僅是新西醫處方葯的原始材料。這應該是喜,還是憂呢?文章引用竇金輝所說,“青蒿素類葯成為首選抗瘧葯,拯救了百萬兒童的生命。它的起跑線是從中醫藥開始的,青蒿素衍生物已經不再是中藥,但是屠呦呦教授從中醫藥的歷史用藥受到啟發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摘自《中藥“赴美”做Ⅲ期臨床,離新植物葯上市還有多遠》|遇見竇金輝2015-11-02零捌叄期)從我自己的診所來看,20年前主動尋求Herbs者大概占門診的70%,包括湯藥和丸藥,現在主動尋求湯藥的已經基本上沒有了,丸藥應用量也大大減少。我主動開給他們,也要費一番口舌:“我只從美國大的合法的食品公司買這些食品補充劑,從來不會從中國直接買,如果有毒,在美國進口海岸會被檢查出來,根本進不來,我也買不到。”即使這樣說,有不少時候還是會被拒絕,或者委婉的拒吃。有的病人,給他一瓶中藥,應該吃8天,但是過3個月他還會說,“謝謝你,你給我的Supplement我還有,還在吃,”那我就明白了,這是委婉的拒絕,不會強迫他們吃。20多年來,經過“麻黃有毒”,“中藥有腎毒性”,“中藥可能導致癌症”等一波波宣傳,人們的概念已經從20多年前“自然產品,沒有毒,比西藥安全”,改為現在“這些自然的東西,成份不明,可能有毒,不能吃”。他們能夠接受寫在藥物說明裡面的正大光明的“毒”,有幾個美國人不吃任何西藥的?看看哪些藥品說明,哪個沒“毒”?不能接受中藥這種“不明不白的毒”。很不願意看到的事情正在中國發生,似乎中國也要學習美國這樣,把中藥當作食品添加劑來管理。問題的核心是:“人類能不能用自然產物作為藥物來治療疾病”?把人體完全按照物理與化學結構來研究的西方思維,找不出一條“途徑”,一種方法(tool),來實現這個想法。吃的東西“,按照美國這樣分為二類更”科學“,還是按照中國概念分成三類更”科學“?冷靜的從人類健康這個大前提出發,起碼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總體來說,中藥的副作用比化學藥物的副作用要緩和得多,”精通“中西藥的”明白人“自己生病會先試中藥,不效再用西藥;醫學模式從局部向整體的轉化,單純的生物醫學模式正在慢慢轉化到社會心理生物醫學模式,那種把人當作化學與物理結構來治療的思路早晚會變。所以”吃的東西“分三類,或者藥物分成兩類,化學藥物,自然草藥,這是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目前的問題就是兩個:一是整個世界分類概念的改變,在食物與藥物之間加出一個”自然藥物“的類別,承認某些自然產品是可以治病的,必須由懂得它們的人處方管理。二是其研究方法不能循西醫研究方法的老路,完全化學分析,雙盲實驗,也不能完全是中醫的經驗醫學和哲學推理;要找到一種讓西醫和中醫都能接受的”雙贏“方法,即讓西醫”服氣“,不得不”承認“,又能讓中藥堂而皇之的治病,而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似乎有點兒”偷偷摸摸“的造福人類。一個是分類的概念,一個是研究的方法。這是目前雞同鴨講中藥所處尷尬局面—問題的關鍵。(4)中美中藥譯差自從西醫”闖入“中國,譯差就開始了,而且從來沒有徹底”明白“過。據毛嘉陵《第三隻眼看中醫·百年”洋相“》中,”’西化‘的12個是是非非“,其中第一個是非就是”’禍‘起西醫術語的’中譯名‘“page83。他講到了中醫心肺等臟腑概念與西醫不同。我就想到當年中醫基礎課上,王宏圖老師講”脾為後天之本“,有學生問:”你講脾為後天之本,為什麼有人因病切除了脾臟,仍然可以生活得很好?“王老師的回答至今印象深刻:”我們中醫的脾就不在那兒長著。“人們中經常流傳著許多模糊說法,例如有位78歲的老年人慢性腎衰竭,每天吃黑芝麻,自稱黑芝麻”補腎“。其實,衰竭的腎是西醫的腎,黑芝麻補的腎是中醫的腎。且不說慢性腎衰竭該不該吃黑芝麻,就這個問題的提出,已經有概念混淆。西醫理論腎衰竭該不該吃黑芝麻,講的是蛋白質攝入多少不增加腎的負擔,從黑芝麻的蛋白質含量分析;中醫是從黑入腎的中醫理論角度來說黑芝麻補腎。人類學的看法,”人類學前輩,吳文藻先生曾說,用中國話談論西學,必然已經對學科實行了’中國化’“,引自王銘銘所著《人類學是什麼》Pag5。反過來說,用英文談論中國文化,必然也已經對中國文化實行了西化。這個觀點用來理解目前”中醫中藥“在中美雙方醫學與文化中的尷尬局面再合適不過了。也就是說,一種學科被從它誕生的語言環境,翻譯到非其母語文化環境的時候,就已經深深地打上了新語言文化環境的烙印。”葯“,這個詞,在中文語境中,我們已經用了幾千年,它的概念已經打上了中國文化的烙印,如上一節所述,它是東方概念的”葯“。西方Medicine,Medication,Drug,這些詞也已經用了幾百年,它也打上了西方文化,西醫學的烙印。”直譯“所帶來的概念差,把現在的”藥物“概念弄得十分混亂。這屬於中西方文化習俗不同,醫學體系不同,法律準則不同,國家管理條例不同,翻譯不能完全精準造成的。我把它稱作”譯差“,源自於”概念差“。即翻譯和概念不同造成的理解差異。中藥湯劑被翻譯成”茶“(Herbal Tea),我給某個20歲男孩開的”茶“,被他的媽媽喝了,她說:”太難喝了,他不喜歡,我就替他喝了,免得浪費。“我解釋,那是葯不是茶。她說:我知道,No pain,no gain,只要對健康有好處,我不在乎苦一點兒。再解釋,這種”茶“,每個人是不一樣的。她盯著我看了一會兒,說:”下次去商店看看哪種茶適合我。“哎,那個思維,它就走不到一起,光是碰出火花。英文中的:”Drug,,Medication,Medicine,Prescribed medicine,Herbs,Herbal Medicine,Over counter Medicine,Supplement“在翻譯的時候全可能被翻譯成”藥物“。可在英文語境中的概念,千差萬別。Medicine泛指醫或葯,用得比較廣泛。Medication泛指藥物,藥劑,用得也比較廣泛,大部分人的基本概念中仍然是化學藥物。因為美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各個不同民族根據自己的文化背景,對它的理解有區別。Drug是治病的,一般指化學藥物,作用強烈,必須有醫生處方。Suppliment是食品補充劑,它不能治病,不能有強烈的副作用,維生素屬於這類,全世界各個不同民族的草藥如果被批准上市,都在這個類別。Over counter Medicine是非處方葯,擺在藥房里,大家可以隨便買,其作用比處方葯要輕得多,類似中國人概念中的維生素,一般的止痛片,退燒藥等等。Herbs是草,沒有葯的概念;Herbal supplement草做的食品補充劑,也不被用來治病;Herbal Medicine這是一個非官方用語,為了把東方概念中”葯“的含義放進去,也想說它們不是”食“。這個詞沒有官方解讀意義,很多中醫師對病人這樣說,大家都這樣用。美國人也懂,但是與他們的”drug“概念還是有區別,頂多他們會理解為維生素之類的”Over Counter Medicine“;Herbal Medicine再翻回中文”草藥“,又變成中文語境的”葯“了,中國人會理解為”葯“,即西方的Drug,其實那不是同一個概念。諾將頒獎給屠呦呦老師時,您注意那個英文稿,他們可以用”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因為”Medicine“的概念比較廣泛,但是講到青蒿素的時候,就是”anti-malariadrug artemisinin“,抗瘧化學葯青蒿素。他們特別希望外國藥廠多多研究中國的草藥,目的是什麼呢?”approval ofnew drugs“,是發現和批准新的西醫化學葯。一般來講,在法律與官方管理概念上,中藥與治病的西藥絕對不是一回事,準確地說,現階段,中藥只能被翻譯成:Herbs,herbal supplements。維生素在中文裡面,你也可以叫做”葯“吧,也輔助某些疾病的治療吧,但是與洋地黃,青黴素,氯沙坦等處方葯不一樣。在美國銷售的中藥都不是FDA(美國食品和藥品管理局)批准的”藥物“,它根本就不是”葯“,一般是以食品補充劑名義進口。因此,開中藥方,不需專業執照認可,誰都可以開中藥方。中藥在美國作為食品和膳食補充劑上市出售有法律明文規定,不可提及其醫療功能。FDA出台《天然植物藥品研究指南》(草案),對中藥的開發也提出了一種不同常規藥品的管理方式:”(a)允許中藥在保證質量控制的前提下,可以以多種成分混合製劑形式進入臨床開發。(b)在美國已按飲食補充劑形式上市,或已有他國臨床資料,FDA將放寬對該葯臨床前研究的要求。通過臨床申請認可後,可直接進入臨床開發。(c)如果通過對照性臨床試驗,證實其安全、有效,便可被FDA批准為新葯。“請注意這最後的兩個字,”新葯“,它已經變成了Drug。也就是說,說來說去,就是Food變Drug。沒有我們東方人分類中的草藥這個概念。(5)”譯差“造就的一個新興的行業。我曾經應朋友之託,幫她了解在中國熱賣的xxxx中藥,被稱為美國FDA批准上市的中藥,在美國的銷售情況。我去了兩個最大的藥店:Walgreen和CVS,店員根本沒有聽說過,也沒有賣過。又去了本地的中藥店,也沒有見到。問過我自己有相同疾病的病人,他們也沒有聽說過。回來用英文上網查,沒有見到。用中文一查,真是熱鬧,確實如朋友所說正在熱賣。仔細研究一下那個”上市“的批准文件,那就是一個允許生產和銷售食品的”公文“。由此我知道,似乎現在有一種新興的行業,中國人在美國有些營養品生產或者加工廠,主要從中國大陸進口某些中草藥進行加工,成為美國的”營養補充劑“,返銷回中國,就成了這些”中藥已經被FDA批准上市“。這些產品在美國的主流藥店,食品店和英文網站是看不見的。美國的”老百姓“根本不知道,而在中文的網址上鋪天蓋地。或許因為,①國內市場大,有比較大的需求;②國內人現在比較有錢,生意好做,比較好賺錢;③人們在心理上對國內的產品有不信任感,怕假,怕上當,怕有毒;④人們在心理上對美國的產品比較信任,只要說是美國進口的,就比較相信,比較好賣。它的特點是:國內熱,國外冷;中國人熱,美國人冷。他們打了一個”譯差“,”概念差“。無論如何這個”擦邊球“打得好,對中美雙方的GDP發展都有貢獻,給美國創造了可觀的就業機會,為中藥找到了更多市場,而作為醫生我只看效果。中醫藥的概念差與譯差造成了目前中藥一定的濫用與禁用的後果。不過話又說回來,發展靠的是機會,中藥概念差與譯差為中醫中藥按照自己的模式在美國開拓發展帶來了機會。完全按照美國思維及法規那麼中藥是進不來的,完全進入西方思維與法規在美國發展,中醫藥就變味了,權宜之計只能目前這個樣子。2000年6月30日,本地中文報紙,《達拉斯新聞》《達拉斯時報》同時刊登了本人的一篇文章”中草藥急需立法“,從此一直呼籲:把有較強毒副作用的中藥列出清單,作為”特殊管理食品補充劑“,只能由美國執照針灸師應用。這在美國,自從”麻黃有毒”事件以後FDA是有先例的。當時FDA有文件,麻黃可以由針灸師在診所裡面用,因此也是目前可行的一步棋。長遠看,中美中藥概念融合,這似乎也是關鍵舉措。美國是一個法制國家,任何法律,法規的建立或更改靠的是人力,財力。人力靠的是利益與共識,財力目前中醫肯定差得遠。還需要更多同道與民眾清醒認識狀況,理解處境,共同努力。[圖擷取自網路,如有疑問請私訊]
|
本篇 |
不想錯過? 請追蹤FB專頁! |
| 喜歡這篇嗎?快分享吧! |
相關文章
熱爆話題